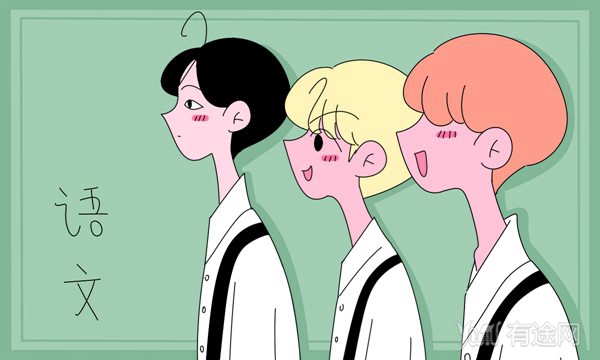热门推荐

2022高考语文议论文名人素材

高考语文议论文人物素材积累

高考语文必背名人成功事例作文素材

2022新颖的作文套用万能素材

高考新颖的语文作文素材名人事例

高考语文议论文经典开头素材

高考语文作文万能开头素材

2022年最新人物作文素材

2022高考作文优秀素材摘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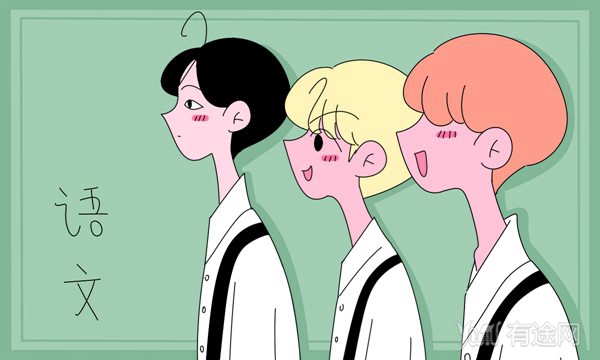

写高考语文作文的议论文必须要有大量的议论文素材作为议论文内容的支撑,下面有途网小编跟大家分享一下高考语文作文素材,希望对你有帮助。

唐人孙樵写过一篇《书何易于》的文章。说的是:四川有一太守,喜游山玩水。一日,他泛舟宜昌县时,因船大水小,屡屡搁浅,便令县里派农夫拉纤。无意间,这太守发现纤夫中有一白面书生,就问是何人,那人答道:“下官是宜昌县令何易于,因春耕时节,农夫忙甚,抽人不易,故下官也来充一名纤夫。”太守听了,羞愧难当。何易于平日勤政爱民,穷苦百姓无钱办丧事,他拿奉银赠与;见到老弱病残等来官仓完粮,每每邀之进餐;自己的随从,不过两三人。因此,三年内把宜昌治理得“狱无系民,民不知役”。
孙樵在《书何易于》中说,何虽“不得志与生时,必将传名于死后。”果然,《新唐书》把他作为廉吏为之立了传。
公元前496年,焦急的子贡四下询问走失了的老师孔丘,这时候有一个郑国人对他说:“东门口有一个人,他的额头像唐尧,他的脖子像皋陶,他的肩膀像子产,可是从腰以下比夏禹差三寸,瘦弱疲惫的样子好似丧家之犬。”子贡找到孔子后把这话告诉他。孔子笑着说:“他说的形状,那倒未必。但说我像丧家之犬,是啊!是啊!”这就是孔子,一个浑身上下充满幽默细胞的老头儿,全然不是千百年来端坐在画像中,端坐在中国人意识深处的“大成至圣先师”的形象。在孔子眼里,要想真正不朽,不在于权力,而在于文化与教育。所以后来儒家称誉孔子为“素王”。没有土地、没有人民,只要文化存在,他的王位就永远存在。
鲍勃·胡佛是个有名的试飞驾驶员,时常表演空中特技。一次,他从圣地亚哥表演完后,准备飞回洛杉矶。在300英尺的高空,两个引擎同时出现故障。幸亏他反应灵敏,控制得当,飞机才得以降落。虽然无人伤亡,飞机却已面目全非。胡佛在紧急降落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检查飞机用油。正如所料,那架螺旋桨飞机装的是喷射机用油。
回到机场,胡佛要求见那位负责保养的机械工。年轻的机械工早已为自己犯下的错误痛苦不堪,一见到胡佛眼泪便沿着面颊流下。他不但毁了一架昂贵的飞机,甚至差点儿造成三个人死亡。飞行员显然应该对不慎的修护工大发雷霆,痛责他一番。但是出人意料的是,胡佛并没有责备那个机械工,只是伸出手臂揽住工人的肩膀说:“为了证明你不会再犯错,我要你明天帮我修护我的F-51飞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陆军反间谍队的高级官员伯尼·费德曼,在一次战地值勤中不幸被德国军虏获,鉴于费德曼的特殊身份为了从他嘴里掏出所需要的情报,德国审讯员施出了种种手段:严刑拷打,心理压力,耍弄诡计,给以厚遇。然均未奏效,以至于德国审讯员无奈地道:费德曼大概愿意我们折腾他,这样给他机会成为英雄。但这位铁打硬汉,最终却被出卖了——出卖他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的弱点,
原来德国人后来把他送入德国一所培养领导间谍的干部学校去,并让他每人陪同一个教官上课。这位教官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每次讲给学员的东西大都是错误的。起初,费德曼极力忍耐,冷笑置之。有一天他实人忍无可忍,便情不自禁地批驳了德国人一通,并谈了美英机关一些工作的内幕,还向德同人提了一些应该怎样搞清通讯网的建议。自然,这些正是德国人希望知道的。
费德曼的悲剧,在于他不容亵渎的职业神圣感和其强烈的敬业精神。德国人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将欲取之,乃先诱之,刺激得他“一时技痒”,在维护他的职业尊严中落入对方的圈套。